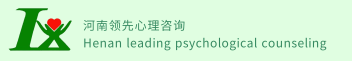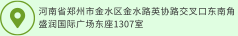20年前,我试图自杀 | 20年后,我成了治疗师
更新于 2018-01-09 | 浏览次数 0
(一)
20年前,我租住在一间狭窄的米色公寓里,老旧的橡木地板破损不堪。我一遍又一遍的擦着那些污垢,但徒劳无用。
那时,我正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想要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在那之前,我从事自杀热线的志愿者已经很久了。
我的咨询技术或许帮助了很多人,但却没能帮到我自己。
抑郁症一直纠缠着我,伴随着它的,还有无穷尽的焦虑,深思和失眠。
· · ·
我总是专注于一些细微的瑕疵,就像我公寓地板上的污垢。我刚搬进去,房东承诺要做地板专业清洁,一直没兑现。
我对此大发雷霆,但又恨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跟她签订纸质协议。进而,我又开始讨厌自己,为什么对于这个脏的地板这么耿耿于怀。
我夜复一夜地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在数小时后醒来。
沉浸于如此强烈的自我厌恶感之中而无法再忍受我的生活。
我注视着地板,一股强烈的自我厌恶吞噬了我。
我感到惶恐,怎么会有人喜欢像我这样的人呢?
(二)
我的抑郁症就像是一个黑暗的存在,自12岁后频繁就发作。
在我26岁那年,我开始服用抗抑郁药,这曾给到我巨大的帮助。但之后我开始掉头发——一种不常见的副作用,因此我停止了服药。
我的新治疗师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希望我尝试一种新的抗抑郁药,但我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认为没什么能够帮助到我的。
即便有,我也不配拥有它。
· · ·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
在外面,我表现的很正常,我古怪的幽默感常常逗得别人发笑。我在心理咨询和精神病理学上表现出色。我的好奇心和敏感度推动着我对人的心灵,大脑以及如何帮助别人进行尽可能多的了解,尽管我始终没法帮助自己。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白天的时候充满活力且热爱社交,但到了晚上大脑中就充斥着孤独又悲惨的想法。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忍无可忍了。我知道这种痛苦的感受是无穷尽的。
对我而言,似乎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彻底终结它。
我呆在我的公寓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母。我为自己给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伤痛道歉,并向他们保证他们没有了我一定会过的更好。
我很肯定这数个月的撕心裂肺的伤痛,要远远好过我继续存在会给他们带来的数十年的痛苦,不确定和恐惧。
然后我用粗马克笔写了另一张纸条“请不要进我的房间。直接拨打911吧,我很抱歉!”
因为房间没有门,我在门廊上缠上包装胶带,并将纸条粘贴在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方。
这样当我2个有我房间钥匙的朋友过来找我时,就会看到它。
(三)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已经是20年之后了,在丹佛大学的办公室里。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终身副教授,我教授心理治疗及精神健康评估的课程,我还拥有一家心理治疗机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专注于自杀风险评估及干预,所以我常常被称为“临床自杀研究专家”。
我创建的网站SpeakingOfSuicide.com,在最近三年访客量已经达到150万。
我对自杀预防如此有热情是因为我知道,不管是从我的个人经历还是其他人的,生活是变得有多么灰暗才会让人相信光亮永不会再来。
但我的热情也激怒了一些访客。他们通过评论留言及邮件的方式指责我根本无法理解自杀者的想法。
一个读者写道:“是,你是读过精神疾病的书。你有一个不错的学位。但如果你从未抑郁、没有试图自杀,你就完全没有资格来写这种文章。”
我一直把我的自杀经历对外人保密。
我承认我感到羞耻,对我自己患有跟我的来访者一样的精神问题,感到非常羞耻。
· · ·
最近几年,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精神健康专家,例如心理学家Kay Redfield Jamison和 Marsha Linehan,都说出了他们自己身患精神疾病及自杀的经历。
越来越多从自杀尝试中幸存的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曾经因为太过害怕,而不敢参与这些对话。但我的沉默,是在跟污名化同谋这一点也让我感到自己的伪善。
其他人的开放态度也鼓舞了我。我仍旧感到害怕,但或许,了解到许多看似坐在幸福的高椅上的教授,其实是跟他们坐在一起这一点,是可以安慰那些身患精神疾病的人的。
在奥斯汀的那一晚,我曾坚信自己不会好了。尽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但我深信我的痛苦是自作自受。
在我贴上写给朋友的纸条后,我把给父母的信放在梳妆台上,旁边还放着我的银行卡以及一些亲密朋友的联系方式,这样我的父母就可以通知他们来参加我的葬礼。然后我开始执行一个我以为会让我平静的死去的自杀方法。
但我的身体开始反击。我的自杀方法中包括窒息。当空气减少时,我的肺开始喧嚷它的需要。我的胸部剧烈浮动想要获得氧气。我本能的大口的攫取空气直到一点都不剩。很快,我的双手开始刺痛,我眼前一片空白。近乎疯狂的,我尽可能快的移动着,最终放弃了这次自杀。然后我开始大口的喘气,一遍又一遍,似乎是在对我饱受摧残的肺部道歉。
一些自杀研究专家,在解释为什么近乎九成的自杀幸存者不会再选择自杀时,说道自杀状态其实是一种解离状态。根据这个理论,自杀尝试硬生生的将这个人带回到他们的身体本身,将个体跟其生存的根本必要性重新联结在一起。
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在我没有办法呼吸的那些瞬间,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想要终结我的生命。我想要终结痛苦,困扰和那些扰动的思绪。而我其实可以在活着的同时想办法来达到这一点。
第二天早上,我将给朋友的纸条取下,打电话给我的治疗师,然后开始服用另一种抗抑郁药。
我开始我漫长的征程,从自杀者到自杀研究专家,不仅是一个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也是一个精神健康专家,同时伴随着这两种身份带给我的所有矛盾,恐惧,希望以及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