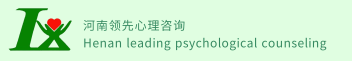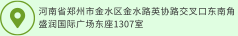「我们治疗抑郁症的方法: 出门去给奶牛挤奶」
更新于 2022-03-26 | 浏览次数 0
「看医生吃药都治不好的精神病人,被两个农民治愈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好奇?这就是纪录片《治愈之家》讲述的故事。
1987 年,瑞典创办了一个家庭关怀基金会,将那些在传统体系中治疗失败的精神病人们寄放在瑞典的农场家庭里。这些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一点精神和心理专业知识都没有,甚至不知道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是什么意思,就是和这些病人生活在一起,吃饭、聊天、遛狗、给奶牛挤奶……
很神奇地是,每个人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后,疾病都会或多或少地有好转:有人不再想自杀了,有人逐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这一现象引起了纽约一位精神科医生的好奇,于是他带着摄像机走进了这个农民之家,想看看那些「破碎的心」是如何在这里得到修复的?
(提示:本文不否认精神疾病传统疗法,以下内容也不能取代专业治疗。)
01
安肯和尤纳斯是一对农民夫妇,作为被基金会选中的农场家庭,他们带着两个儿子,和不定期来寄宿的精神病人们一起生活了 20 年。
影片一开始,导演就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愿意做这些?」——和精神病人们一起生活,并且帮他们疗伤。
尤纳斯夫妇说不上来原因,而是讲述了他们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
一位单身父亲离婚后作为难民带着孩子来到这里,42 岁的大男人,不会说英语不会说瑞典语,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痛苦地躺在地上嚎叫。
「把你放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自然会知道怎么做,你就是普通人。」说到这里,男主人尤纳斯流下眼泪。
17 岁的女孩,刚来到农场时有非常严重的自残,脏话连篇,会在愤怒的时候把整张桌子掀翻。
女主人安肯也很生气,但她心想着:「我看见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我一定得做些什么。」于是用全力按住女孩的胳膊坐在床上:「现在停下来。」
半分钟后,女孩开始大哭,她紧紧地抱着女孩:「呆在这儿,试图留下来,我们一起解决。」

02
「为什么每个住进来的病人和尤纳斯夫妇在一起都能感觉到安全,如此安全以至于愿意敞开心扉呢?」
导演惊讶地发现,区别于传统疗养院,在这里病人和监护人的界限已经不再。每个住进家里的病人,都被当成了家庭的一员。
在尤纳斯夫妇看来,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从来不用客户这个词,而是直接称呼名字,如果邻居问起就说「她是我的表亲安娜,安娜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她有一些麻烦。」
安肯在每天的工作日志里会用「我的朋友」称呼病人。
他们从不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会生气、哭泣、开心。「我们和其他人没有区别,这样他们才能展示自己。」
作为一个父亲,尤纳斯觉得能在孩子们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绪是很棒的事情。
03
当被问到是什么让他们的家庭能够有如此治愈力的时候,女主人安肯说:「我认为是整个家庭,我们的狗也有帮助,还有畜栏里的动物。这些日常事务很重要,让你的生活重回正轨。」
尤纳斯夫妇家里有一个农场,养着很多奶牛,作为家庭成员之一,每个病人都需要承担一定的奶牛照料工作。
一位十几岁的女孩来的时候,有严重的心理创伤,总是在不停地哭泣。一开始安肯会耐心安抚,但到了喂奶牛的时间就会打断她:「我们不能站在这里说话了,我们必须出去喂那些奶牛」。
时间久了, 女孩慢慢地愿意和咨询师分享一些事情——给奶牛喂饲料、挤牛奶、把奶牛的身体擦拭干净……
「她和奶牛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就是治疗的开始。」咨询师说到。
04
导演是来自纽约的精神科医生,在他看来,面对那些没有服药的精神病人,即使是医生也会有几分不安。而尤纳斯夫妇则是把病人邀请进家门,然后锁上门。
「当他在地上爬行,并且发出奇怪的叫声时,你难道不害怕吗?」聊到一个病人的故事时,导演问到。
「我们从未怕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一个人在地上爬来爬去,感到伤心和迷惑可怕得多的事。」尤纳斯回答。
导演和他们还聊到了自杀——提到精神病人很难回避的问题。在美国传统治疗体系中,防止他们的客户自杀是医生很重大的责任,有时候为此反而剥夺了病人的自主权——病人反而被试图帮助他们的体系伤害。
但尤纳斯夫妇不认为作为监护人应该为病人的自杀承担责任:「我们会问自己,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吗?凭良心说,如果真的尽到了最大的努力,那自杀就是他们的责任。」
05
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安肯和尤纳斯夫妇并不具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分不清「精神分裂」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也不想去了解。
来到农场后,面对那些常年用药量很大的病人,为了减缓药物副作品,尤纳斯夫妇还会帮助他们减少用药,把药片切地越来越小。因为他们认为精神疾病是心灵的创伤,很难通过药来治愈。
但他们做了很多其他事情来取代减少药物的作用,「我们一起遛我们的狗,我们也一起喝茶、讨论,有时我们一起哭,我们也出去到畜棚去挤牛奶,我们整天都呆在一起。」
偶尔也会遇到让尤纳斯夫妇棘手的病人。有个女孩来之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没办法在城市里生活,她彻底地发狂,无论去到哪里都会被抓起来,甚至没办法办一张银行卡。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尤纳斯夫妇和她聊了两个半小时,她不停谈论帽子下面有冷冻鸡胸肉的女人。
因为完全无法沟通,尤纳斯夫妇也觉得压力很大。于是那个女人有时候一周来家里住一天,有时候住三天,就这样按照双方都舒适的节奏,经过长达三年的时间,她最终还是平静下来了。
后来她逐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了银行卡,尤纳斯夫妇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我从瑞典飞到荷兰,从荷兰到美国,最后到了洛杉矶。感谢你们,感谢那些帮助。」
整个片子看下来,你会感觉尤纳斯一家人身上仿佛有一种让人能安下心来的魔力。
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尤纳斯夫妇的大儿子刚从畜栏工作回来。他从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看着家里来来往往的病人们,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