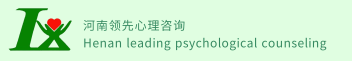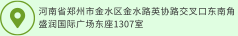易性癖乃上帝的误笔
更新于 2015-12-05 | 浏览次数 0
他是一个男人,却有一个女人的名字:阿婷。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于是,不得不流浪于夜总会做“歌女”,在其中尝一尝做女人的滋味。
他身披薄纱,像一缕细长的轻烟,袅袅升到舞台中央。带着莲花般娇羞的浅笑,歌声如夜雨,星星点点洒进每个人的心房。
台下嘘声连片,有人紧盯他的胸脯,有人嚷道:“我看到了他的胸毛!”还有人大叫:“脱下你的衣服!”今晚,金舞鞋酒吧座无虚席,迷离的灯光里,一双双惊愕的眼睛,为一位异乡女子的表演而倾倒。
有主持人介绍:“她”并不是女性,“她”是个真正的男人,只不过做反串,男扮女装。有人仍不想信,追着她问:“喂,真的假的?”“喂,你是不是人妖?”
我们见过京剧反串和越剧反串,那是一种艺术;我们听说过人妖,那是对男性的摧残,我们还听说过变性,那是边缘人的痛苦。
“她”是一个男人身,但“她”却拥有女人的相貌和身材、嗓音和姿态,以及一个女人的名字:阿婷。阿婷对追问者说:“阿婷不是人妖,阿婷没有做手术。”
然而,阿婷的梦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做一个女人,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亭亭玉立的女人。
1976年,阿婷出生于广西。阿婷有六个姐姐,他是第七个,他是男孩,是这家唯一的儿子。父母给他取名叫军军,希望他像解放军一样样勇猛坚强。
军军由姐姐们带大,穿花衣裳,玩女孩子的游戏。姐姐温暖的怀抱是他最安全的港湾。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男孩,是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不自觉地随一群女孩子走进女厕所,却被阿姨喝住了:“李小军,你走错了,你该上男厕所!”他睁大了眼睛,从来,姐姐们都是带他进女厕所的!从这一天起,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扮演女孩子了,他是个男孩子,必须和其他男孩一样进男而所,并站着尿尿。否则,真正的女孩子就要骂他“流氓”!
那时候他还小,无所谓。
真正有所谓时是在14岁,他读初中。他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像男孩,其他的男孩生龙活虎,活泼爱动,健壮有力,声音响亮。而他,胆小怯懦、瘦弱单薄、斯文内向、声音细小。他越来越像个女孩子,越来越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玩,他梦想着自己也能像她们一样穿上美丽的花衣裳,扎上美丽的蝴蝶结。
可是,女孩子并不欢迎他,男孩子都嘲笑他,叫他“贾宝玉”、“假小子”。
我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哭哭蹄啼啼地去问姐姐,他像一个愤怒的猎手,在森林里到处开火,却只打下一些黄叶。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他疯狂地去图书馆翻书。他把所有所有的医学书都找来看,而在一本收理学书籍上,他找到了自己。心理学家用三个字圈定了他漫长的人生——易性癖。合上书时,他的头有些晕,仿佛书架上的书噼哩叭啦就要倒下来压在他身上,而那三个字却划着圆圈在他眼前旋转。
男孩上男厕所,女孩上女厕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理所当然得让人简直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回家的路好漫长。每个人都在匆匆赶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唯独他没有,便不知道这路怎么走。
这年暑假,他从家里偷了些钱,坐火车到天津去找陈仲舜,他在一些杂志上得知陈仲舜是一位着名的心理咨询专家,他以前给一些易性癖患者作过咨询。
火车到达天津时已是零时的夜晚。他在车站随便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阴暗潮湿的房间,蚊蝇乱舞,被子隐隐发出一股霉味。而他的脑子里,却无数次美好地勾勒着陈的形象,欣喜如那股霉味,在他的呼吸里弥漫。
他找到了陈的心理诊所,站在门口,却迟疑了。他只不过还是个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向陈诉说他的矛盾和痛苦。就算陈能理解他,能听他诉说,但是,他能帮他变成女孩吗。
当夏日的阳光烤得人有些发昏的时候,当街上的行人开始用狐疑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这个少年的决心像受潮的糖塔般在阳光下涣散成碎片。他呜呜地哭着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落荒而逃。陈自然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个14岁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向他求助,却连他的面都不敢见。坐在回家的火车上,他长吁一口气。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宁愿将自己身上的脓疮捂着藏着,却不愿意一刀割去。他害怕自己像洋葱一样被一层层剥开,害怕陈给他他诊断之后也会给他下和那本心学书上同样的断语。这恐怕才是这个孩子怕见陈的真正原因。
心里的石头终究没有放下。也许,那块石头将会摇呀晃呀陪他走完这一生。
17岁时,他越发出落得像个女孩。身材窈窕,皮肤细滑。同龄的一个男孩蓝对他格外青睐,常常给他一种类似男孩对女孩的暧味的眼波。蓝搂他的肩,握他的手,与他耳鬓厮磨。蓝说:“军军,如果你是个女孩,我真的会爱上你。”他耳朵发烧,心砰砰地跳,突然对伴了自己17年的名字感到一阵恶心。他对蓝说:“叫我阿婷,女字旁的婷!”蓝猛地将他搂得更紧。
蓝极大地鼓舞了他。有什么比爱情更重要?他开始放肆地留长发,穿掐腰的衣服,轻盈地举步。他吃许多激素以及含有激素的药丸,甚至避孕药。变化是在一天一天。她像女孩一样长出了丰满的胸脯,皮肤像女孩的一样光滑细腻,身段像女孩一样婀娜多姿。
他不敢理直气壮地穿女装,然而他穿什么男装都像女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身上都粘着许多怪异的目光,一些声音汇成一条河,向他汹涌而来。“瞧,那个人不男不女!”“看那个阴阳人!”“他变态!”那些声音穿透了他的背,凉飕飕直指他的心脏。
“你这样伤风败俗,连累我们全家跟着你丢人!”父母流着泪数落他,他们毕竟是有头脸的人物,那个城市几乎一半的人是他们的关系网。
我比女孩更漂亮更温柔更善良,为什么我却不是女孩?命运似乎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他无路可逃。他吞下了整整一瓶安眠药,被家人呼天抢地地救回来。身体有半年时间像脆薄的枯叶,由于安眠药的腐蚀,他的五脏六腑像有铁丝穿着,一牵一扯地疼。
皮肤逐渐变得粗糙,汗毛加深,毛孔粗大。他伤心欲绝,激素更加片刻不离。
当19岁的春天抽出嫩芽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乡,也彻底告别了蓝。他发誓,就是饿死,也绝不回来。家乡都是熟人,家乡没有活路,他迟早有一天会枯死。
在离家很远的城市,他靠打工养活自己。在一家酒店做侍应生时,一个大款模样的人色迷迷地盯了他许久,于是,他的命运就在那天晚上走到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点,到大款开的娱乐城里做反串演员。
这无疑让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延续。在舞台上,他可以尽情展示女性的魅力,可以随心所欲、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做女人,说女人话,化女人妆,穿女人衣,唱女人歌。
“阿婷”从此成了他正式的称呼。台上台下,没有人知道军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阿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唱的第一首歌都是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白天蜇伏,晚上演出,在舞台上,他已经是个迷失的灵魂,扭曲的灵魂。掌声如潮,喝彩声声,他不过是客人眼中的怪物,男人手中的玩物。舞台能够让他做女人,他只有这个选择。
时光之箭射落岁月的一些枯枝败叶,有些事物却一年一年呈现新绿的色泽。阿婷的痛苦便是如此。时光流逝,阿婷长大,他的痛苦却新鲜如初,胶着不散。
“我要做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声音像来自地底,遥远而执着,一年比一年强烈地撞击着他的耳鼓。吃激素,表演,直到有一天躺到变性的手术台上。
冰冻的时分,零时的夜晚,一个漂泊的灵魂,独自茕茕,在夜归的路上拼命挣扎。